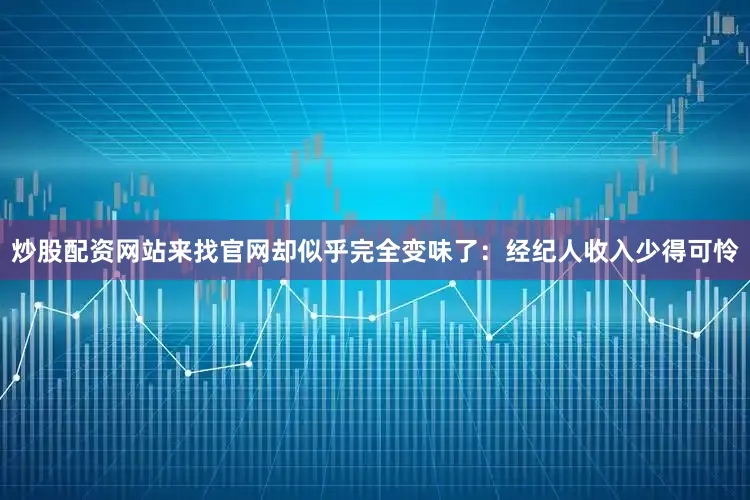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
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只吃一口就不吃了,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
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
为什么不对?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
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
(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
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
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
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
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
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
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
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
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
上网配资炒股,最好的配资平台,股票配资广东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北京网上炒股配资网贝森特: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仓促行事
- 下一篇:股票配资平台查询网站